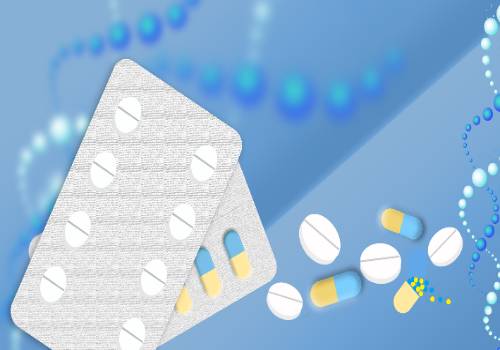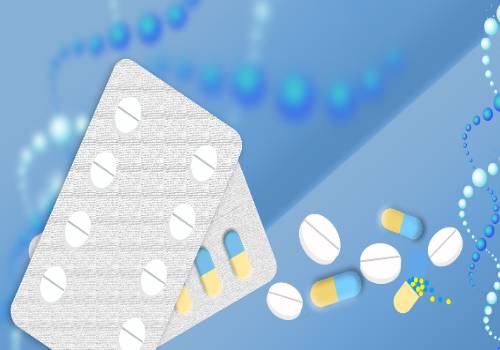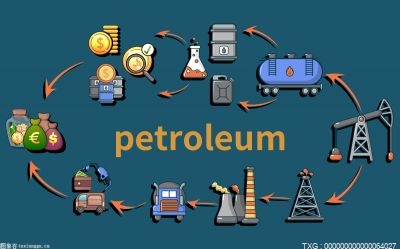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李渔,编辑:灯灯,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在我国,植物人患者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群体。医院不愿收治,养老中心不接纳,绝大多数植物人只能在家中由家属照顾。由于家属往往缺乏护理知识,过早地黯然死去,是不少患者的最终结果。
2015年,相久大辞去北京市密云区医院门诊主任的工作,创办了国内唯一一家植物人托养中心,为植物人患者和家属提供了另一个选项。7年多的时间里,一共有200多位植物人患者在中心里延续了生命,安宁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对于相久大而言,这是一条孤独而又艰难的路。作为“生命边缘里的摆渡人”,他说,每托起一个植物人的尊严,等于安放了一个家庭的心灵。
十点人物志走访了这家植物人医院。
植物人的世界
晚上十一点十三分,延生托养中心的病房明亮依然。
九位患者在灯下“睡”得正深,从房间最东侧,依次排列到房间最西侧。灯光茫茫如雪,映照在瘦骨嶙峋的面孔上,却映照不出半点清醒的迹象。病房里没有呓语,也没有鼾声,只有微弱的嗡鸣声正隐隐传来,那是制氧机发出的声响,除此之外,就再也听不见什么了。
这是延生托养中心的一个普通夜晚,这些病人都是植物人患者,安宁的病房里形如空寂的山谷,初次来访的人,难免会有窒息和压抑的感觉。不过,对于五十三岁的相久大医生来说,这样的场景,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养护中心病房/图源受访者
相久大创办的延生托养中心位于北京市密云区,这座僻静的乡村院落里,共居住了四十一位植物人患者,最大的八十四岁,最小的只有三十八岁。他们或发生了事故,或遭遇了急症,就此陷入了沉睡,失去意识的躯体就仿佛一条一条搁浅的鱼,被禁锢在了四五平米大的病床上,从日出到日落,二十四小时里,鸦雀无声。
在童话世界里,公主若想醒来,只需要一个轻轻的吻。可惜现实不是童话,陷入持续植物状态的病人,几乎没有再次恢复的可能性,无法苏醒的人生就像一朵正在枯萎和凋谢的花,悄无声息地滑向死亡。
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只有相久大和他的护理人员们:24小时待命,帮病人排便、喂食、清理伤口、擦拭身体。病人突然咳嗽,护理人员便立马上前叩背排痰;每隔两小时,他们会主动帮患者翻身一次,病人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按下了暂停键,直到下一次护理来临。
没有痛觉,也没有悲喜,甚至于白昼黑夜,在植物人的世界里也没有多少差别。
在病房巡查时,相久大总是小心翼翼,轻轻地端起水杯,轻轻地放下水杯,静悄悄地站起身,说话时轻声细语,明明知道患者一无所知,可是却仍担心自己带来惊扰。
凌晨一点的病房/图源受访者
遥遥传来了狗吠,村子里的家犬醒了过来,不过三两声动静,又突然归于沉寂了。相久大久久注视着窗外,漫无边际的黑夜也正从窗口凝望过来,彼此相互对视着,一个夜晚就静悄悄地过去了。
植物人不是死人
四十五岁以前,相久大的人生履历并不起眼——按部就班地读书、按部就班地毕业,理所当然地进入北京市郊的密云区医院,不惑之年任职门诊外科主任。一切水到渠成,就好像一条小小的河,平平淡淡地沿着既定的方向,一直流淌,一成不变,又波澜不惊。
相久大医生/图源受访者
不过,人生几十年,难免产生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做一线医生的时候,日日夜夜对着病历本和化验单,身上的白大褂穿久了,相久大常常有一种困在原地的无力感。
而就职门诊主任后,告别了听诊器和柳叶刀,陷入日复一日的文山会海,无力感尤其严重起来。那种未来一眼看到头的恐惧,时时追在身后,久而久之,他开始萌发出辞职创业的念头。
但辞职能做什么呢?相久大自己也说不清楚。
创业的医生很少,创业成功的医生更少。在大多数人眼里,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如同驶进一条高速隧道,退也退不了,拐也拐不了,除了开足马力一路向前,似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转折出现在2014年。密云区医院收治了一个脑干出血患者,虽然医护人员尽力挽救了他的生命,但却挽留不回意识。缺氧太久,患者成了植物人。
既然注定无法苏醒,在医院眼里,那就没有继续抢救的价值,“建议家属回家照看”更像是医院对“逐客令”的文雅说辞。患者三个月后在家离世,相久大回忆,“身上都是褥疮,人都臭了”。
结局令人唏嘘,不过也让相久大发现了一个潜在市场。医院几乎不会收治植物人,养老机构也几乎不会接收植物人,病人家属又缺乏专业护理知识,他忽然想到,既然没人愿意接收,那么自己接收不就行了?
于是2015年,相久大正式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带着卖房筹集来的200万资金,创建了全国第一家植物人托养中心。
最初他想开在市区,遗憾的是,从二环跑到六环外,联系了几个地址,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相久大已经付下定金,可业主最后还是反悔了。
原因大同小异,无非是因为“晦气”。有人说房子租给死人不吉利。相久大争辩,植物人是活人,活人租房子总没有问题吧?对方立刻回答,植物人都在等死,等死的人怎么能叫活人呢?
处处碰壁,让相久大一度陷入迷茫。他反复跟人家解释:“植物人跟刚出生的婴儿没区别,婴儿什么都不知道,植物人也什么都不知道,婴儿要人照料,植物人也要人照料。”城市里遍地开满月子中心,为什么植物人却连人都算不上了?
城区容不下他,相久大无奈将目光投向远郊,最后是一个朋友帮他找到了落脚点。
一栋半山腰的小楼,距离密云城区三十公里,距离北京市区九十公里,能够遥遥眺望着燕山山脉和密云水库。除了鸟语花香,更重要的是清净。清净意味着远离人烟,远离人烟就少了许多闲言碎语。
相久大将一半现金花在装修上,又找来了七个护士。养护中心开张的第一晚,照明灯在病房里一个接着一个亮起来,恍惚之间,仿佛雨水一道一道敲打在墙壁上,很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味道。
相久大正要有感而发,忽然之间,山间停电,黑暗重新袭来,顿时伸手不见五指。
孤独的事业
电力不足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虽然隔三差五发生,但解决起来只需要备上一台发电机。真正困扰着植物人托养中心的,是找不到植物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小聪是托养中心里的唯一病人。2012年的飞来横祸,不光让她失去了半片肺叶,就此沉睡,也让她的家庭陷入了困顿。就在全家人走投无路时,有人介绍了相久大的托养中心。
七个护士,加上相久大,八个人整日团团围绕着一张小小的病床,最初三小时去看一次,后来一小时去看一次,最后只要闲下来就去看一次。心电仪上的曲线上升、下沉、再上升、再下沉,默默无声又无休无止,不知不觉,一盯就是一天。
刚辞职时,相久大自己私下算过一笔账——想要收支平衡,十六个病人应该就够了。行医二十年,他积累了许多人脉关系,这个数字并不夸张。
可是被推荐到托养中心的病人,很长时间都只有小聪一个。再去联系以前的同事和朋友,得到的回答往往模棱两可,“再等等”,“以后再说”。他一度夜不能寐,不过现在早已释然了,“这其实很好理解,这行业谁也没听说过,谁敢放心把人交给你?出了事儿要怎么办?”
于是相久大的工作只剩下照顾小聪,以及为了照顾小聪去研究中外文献。白大褂和柳叶刀的日子仿佛还在昨日,累了,揉一揉眼睛,恍惚间还能见到呼啸而来的救护车和步履匆匆的护士跟大夫,清醒了,才发现一切只是错觉。小聪依然默默无声着,山风仿佛口哨,鸟鸣仿佛笑言,心中明明知道她对周遭变化毫无感知,可有时候相久大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其实她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一些呢?
植物人患者/图源受访者
可惜小聪从来没有一丁点儿回应。静悄悄的病房外只有静悄悄的山林,相久大一天做不了多少事情,做一做,停一停,停久了,焦虑的感觉就慢慢浮现了出来。
孤独之外,缺钱也是相久大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现实困扰。
相久大开始在网络上发广告,他注册了一个贴吧账号,在植物人贴吧上面分享起植物人护理的相关新闻和知识,也顺便介绍自己的植物人托养事业,他留言说,如果有植物人家属亟需帮助,欢迎随时联系。到了第二年,病人数量终于有了成倍增长——达到了三个。距离最初的目标依然遥远。
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时,陆陆续续,一半儿护士选择了离开。相久大对此表示理解,壮志凌云固然可敬,但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他继续选择坚持,并不是不在乎柴米油盐,他坦言,自己只是走不了。
至于走不了的缘故,他说:“这跟开饭店不一样,饭店不开了也就不开了,大不了给人家退钱就完事了。但植物人不一样,植物人不是商品,家属托付给我,能说退回去就退回去么?开不了这个口的。”
希波克拉底誓言里说:我要让自己记住,我不是在治疗一张病人发烧的记录纸,也不是恶性肿瘤本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相久大的话简单至极,“没办法,这事儿压根儿就停不下来。”
植物人托养的意义
还在做医生时,相久大常常要经过区医院的老急诊楼,千禧年之前,楼体上曾刷着一行鲜红色的大字:学习白求恩精神。他从大字下经过时从未对此有过太多思考,救死扶伤的誓言就像弥漫在病房里的消毒水味道,理所当然,而且天经地义。
离开医院后,相久大发现救死扶伤不大可能在托养中心里实现,植物人托养的工作更类似安宁疗护以及临终关怀。在最终结果已经注定的情况下,如何让整个过程更加体面,不仅仅涉及到植物人的尊严问题,也是家属在现实和伦理之间的权衡。
对小聪的家人而言,失去生活的并非仅仅小聪自己,从车祸那一天开始,爱人小唐的生活同样被迫画下了休止符。他辞去了工作,二十四小时日夜监护,吃在病房,睡在病房,拍背、翻身、喂食,一模一样的生活重复了两年半。
然而,女儿的成长和物质的压力,并不会因为小聪的停滞而发生任何改变,当一切无以为继时,小唐不得不在现状和未来之间做抉择。
小聪被送来的那天,相久大说,“放心吧,我们保证会好好照顾”。当希望渐渐化作泡影时,活下来的人终归要为了新的希望努力活下去。
后来小唐去了南方,重新开始了中断的事业,对小聪的探望变得断断续续起来,偶尔出现,总要举着手机给远方的女儿直播,他说,“叫妈妈”,然后怔怔地望着床上的妻子,彼此一阵沉默。
与此同时,接收的病人越来越多,相久大也开始默默思索起托养工作的定位。他觉得植物人虽失去思维意识,但绝非死亡,而是在正常和死亡之间的特殊状态。
因此,他们就像站在一叶扁舟上,轻轻摇起双桨,将患者从此岸带到彼岸,只留下家属默默、默默地伫立原地,静静目送离开。后来他常常总结说:“这就是让家属慢慢接受死亡的一个过程。”
护士日常护理/图源受访者
也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植物人连意识都没有,有没有尊严还重要吗?
相久大回答:植物人是否有尊严,取决于身边的人如何对待他。
对方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如果植物人无法感知这一切,那托养对植物人本身毫无意义,仅仅是“家属自私地想要延续植物人的生命”。
观点并没有对错之分,只不过相久大无法赞同,他认为这样的说法过分冰冷和理性,而人是需要感情的:“如果因为植物人感受不到,托养就没有意义,那么生者悼念逝者,逝者也感受不到,我们的悼念和哀思也都没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