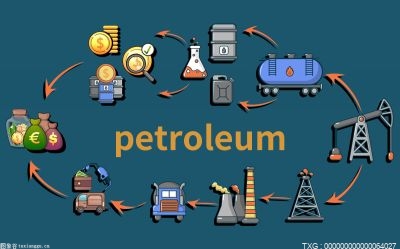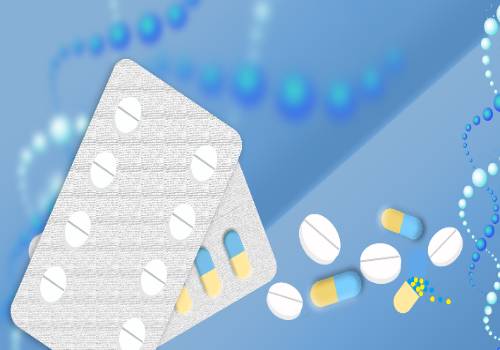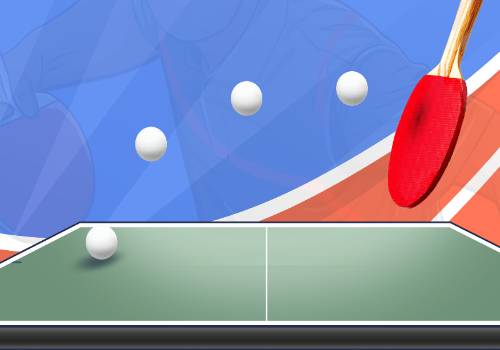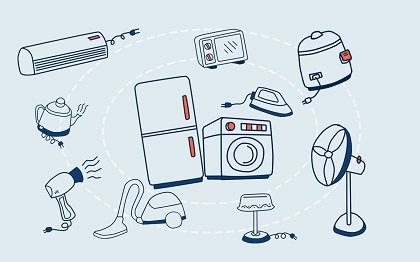引言
古代史研读:室韦与诸政权的关系——以辽朝为例,十世纪之后的室韦与同时期或相继立国的诸政权之间的关系,跟传统北狄诸族一样,对诸政权采取依附、朝贡、侵边等多种形式。尤其辽代,契丹征服室韦后,起初对后者置部统领,继之设节度使、国王府以加强统治。
 【资料图】
【资料图】
可见,辽对周边游牧民族“因俗而治”的统治措施与唐代对北狄族置羁縻都督府统领相似。但不同于唐朝的是,辽朝派遣其核心氏族耶律氏或萧氏直接监管或统领各属部。那么十世纪后的诸政权对室韦诸部的统治政策与前朝相比有何变化?试以辽朝为例略作分析。
辽朝对室韦—达怛、阻卜的统治
自《隋书》起,室韦与契丹就有密切的关系,地域上也南北接邻。而且学界研究成果也多次肯定,契丹与室韦是同属东胡系的鲜卑后裔。那么经过唐置室韦都督府,至契丹建立辽政权后,对昔日被中原人认为同族属的室韦诸部是如何安置的?
对于辽代的行政管理,研究者提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属北面官的宫帐、属国和部族;第二类是隶属南面官的五京及其所属州县。”亦即所谓辽朝治策中的南北面官制,其统领者皆为契丹人。南、北面官又称“南院”“北院”,分别管理辽代南北政区,北方游牧民族属北院管理。其中属国多指归附契丹的其他北方游牧民族,“部”是辽对于征服后的游牧民族的安置,其数量随着契丹族征服周边民族而增多。
辽太祖时期有二十“部”,圣宗朝有二十四“部”,包括室韦、乌古、敌烈、女真、党项等族。辽统治者所置的“部”,用以管理俘虏、降部或奴隶等,将其集中单独安置,使这些“部”成为与原有契丹部落相近的内属部落。所以在辽朝管理体系中的“部”是人为编成的新管理体制之一,用契丹族的统治方式即所谓国制进行统领。
开泰三年(1014),时“室韦查剌及萧宝神奴、谋鲁古并加左卫大将军”。此处的官职受任者应是辽朝直接统治下的室韦部族,而并非室韦原部。辽置的部族制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分布于内地的五国部,后设节度使管治;一类是在辽国统治境内,而在地理位置上属边境地区的部族,置国王府管治,目的是兼顾诸部的本族习俗。
对大兴安岭、嫩江流域一带的室韦地区也置室韦王府统治,奚地置奚王府。穆宗时室韦叛,因而辽圣宗时期,“部”增置节度使,以强化统治。至于国王府的设置,《辽史》记载的时间仍是圣宗时期。辽朝的属部属国体制,大致与唐代为统治周边民族而置的羁縻都督府相类,都是独立性较强,因本国习俗而治的属国统治方式。
不同的是,唐代以其部落酋长为大都督,并使之代袭其职。而辽代起初所置节度使等官,皆由契丹人担任。如“(耶律瑶质)父侯古,室韦部节度使。”又,“宋兵夜袭营,突吕不部节度使萧干及四捷军详稳耶律痕德战却之。”可见辽对内属的室韦与原居地的室韦部统治措施虽有区别,但统领或监管人员皆由中央直接派遣,这也成为契丹维护朝政稳定的措施之一。
辽朝时期的中国东北诸部族中,蒙古高原东部一带的室韦诸部与其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诸部族比较活跃。如乌古部便是其中最活跃的部族之一,因“乌古、敌烈,大部也。”故契丹对其统治尤为重视。
自辽太宗天显五年(930)起,乌古部朝贡频繁,同时叛乱亦多。而且常受辽廷调遣,参与契丹对其他族的征伐。辽对乌古的安置政策也与室韦不同。如辽太宗会同三年(940)“乌古遣使献伏鹿国俘,赐其部夷离堇旗鼓以旌其功。”
旗鼓本是游牧民族权力的象征,可知辽对其部的重视。但契丹统治者仍未松懈,兼派详稳、行军都监、节度使等契丹官员至乌古部,由萧姓族人担任。史载“乌古部节度使萧普达讨叛命敌烈,灭之。”又“耶律蒲奴宁乌古迪烈得都详稳。”辽圣宗开泰三年(1014),耶律韩留迁乌古部都监;“乌古敌烈部详稳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都监萧阿鲁带乌古敌烈部详稳,加左监门卫上将军。”
至于室韦部是否置有详稳、都监,史书无载。但《辽史》中有“黄皮室详稳唐筈皆死之”的记载(而黄皮室或称黄皮室韦)来看,室韦所设官职与乌古等部有相同之处。然而,契丹对乌古的统治与压迫比室韦更为严重,除日常剥削外,甚至以乌古之地水草肥美为由,迁“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其目的为防范乌古部的反叛。
可见,辽对乌古部的安置颇费周章。一方面从地理位置上看,乌古部与辽北疆相邻,且乌古虽在辽太祖时期已被征服,但也时常发生叛乱,影响辽的边境稳定。另一方面室韦被契丹征服后与其关系较为稳定。唐代文献中室韦部落数量不少,但在契丹族的内外施压之下又经历一次分化后,对辽已不构成太大威胁,所以辽对故地的室韦未用特殊管理措施。
辽对阻卜诸部的安置
关于辽对阻卜诸部的安置情况,有学者提出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太祖至景宗时期以朝贡或赐授官号为主;圣宗至道宗中期采属国属部体制管理阻卜各部;道宗中后期以西北路招讨司作为统辖机构。辽道宗会同九年(946),辽以阻卜部酋长为夷离堇。(夷离堇是辽统军马大官,辽太宗会同初,改为大王。)这种较高级别官号的外授,可能是辽朝出于对与其本族组织形式相近的阻卜各部首领地位的认可。
以上所述,辽对室韦部及与唐代室韦存在渊源关系的部族进行分类管制,即都是单独的部族,相互间无明显的联系。但从大的管治体制看,契丹—辽对室韦及其他从室韦部演化而来的内属部族的安置并无两样,皆为起初分别置“部”,对留居故地的部族集中地区则派契丹节度使或监管统治。
然而,因各部地理位置与势力大小不同,在辽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不同,且中后期时,文献中便再无室韦的记载。或许入契丹统治后的室韦,从辽中后期起部落发生演变或名称发生变化,进而辽朝官方文献中少载或阙载。
结语
总体而言,在辽代文献中,“室韦”一词在地理空间上的涵盖范围主要是蒙古高原东部及中国东北地区一带。但其与契丹之间又隔着乌古、于厥等部,故对于契丹来说,室韦的威胁远逊于乌古等强部。而且,此时漠北的阻卜势力强盛,所以辽政权更多注意力并不在仍处于原居地的室韦,而在于蒙古高原上对其统治造成更大挑战的其他蒙古语族诸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