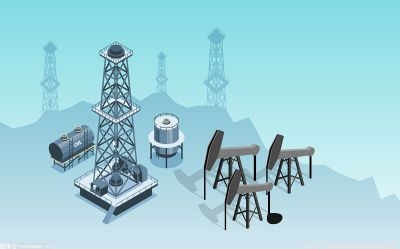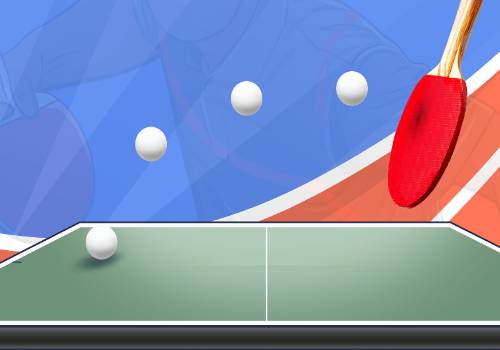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原标题:一个断亲的年轻人躲去南极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撰文|吴向娟
编辑|孙雅兰
出生于河南许昌一个普通家庭的李开,长期过着被父母严密安排的生活,成长中自我意志的苏醒,让他越发想挣脱被动的人生轨迹。
23岁这年,李开搭上前往南极捕虾的渔船,成为一名船员,将自己抛向遥远的无人之境,期望通过断亲实现自我价值的确认。然而南极也非桃花源,他最终发现,要解决内心的迷茫和不安,还是需要回到现实生活。以下是他的自述。
01
上船
来南极之前,我从不知道海能幻化出这么多颜色。我看见夕阳从天边倾泻而下,把海染成金橙色。也见过绿色的海,像是在白色荒漠里淬出的一块翡翠。而当船队漂浮在翻滚着黑色浪花的海上,则有种在末日里狂奔的感觉。
每当遥远的海岸线上浮起雪白的“糕点”,看上去松松软软的,形状不一。我就知道,要靠近岛屿了。这时候,我会点上一支烟站在窗前,沉浸在独属于南极的浪漫时刻。船上规定不许出现明火,但在这个全是糙汉的地方,香烟例外。在风浪里摇晃的渔船,挤着110多位船员,咸腥的海风混杂着汗臭味四处飘荡。
春节期间,渔船驶入南极洲内部,船上彻底断网,并将持续四个月。此前,大家都忙着给家人发消息报平安,我却感到无尽的自由正朝自己走来。
初到南极,眼见的一切都令我兴奋。有时是十几米长的鲸鱼浮上水面喷水换气,在远处溅起两米高的水花。有时是成群的企鹅站在冰山上眺望船队,用嘶哑的叫声向入侵者发出警告。我们还遇到过被塑料袋、绳子缠住的海豹靠近渔船向人类求救。而当误捕到带有剧毒的章鱼时,则慌慌张张地往海里放生。
图|前来求救的海豹
搭上南极的船,对我来说是一场逃离。毕业后的三年里,我一直没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对未来的生活也一片迷茫。陷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如同一艘下沉的船只,逃离是一场迫在眉睫的自救。
上船不到十天,我的皮肤就开始瘙痒、龟裂,被船上的医生诊断为海水过敏,给我开了些涂抹的药。雪山折射的光穿透玻璃,将我的鼻尖照成蓝紫色,映衬出我溃烂的紫红色脸颊,新旧交叠的疤痕层次分明。伤口难愈,一遇风就灼痛,严重时人还会发烧。
过敏的人一般不会在船上久留,而我却已经待了一年。我喜欢南极的偏远和冷清,这儿离我的家乡足够远,离我不如意的生活足够远。
招工的渔船负责在南极海域捕虾,常年往返于南极和舟山之间,出行一趟需要20个月。应聘需要考取船员证,再交一笔三千元的中介费。我以高分通过考试,最终获得这份工作。出发前两天,我告诉父母要去南极了,一个月工资一万多。父母很满意,觉得我终于找了一份正经事。
图|企鹅在船上停留后离开
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和父母一直处于拉锯状态。早在高考结束后,他们就替我规划好未来,但这周密的安排却成为束缚我的绳索,我越是挣扎越是疲惫。
当初因为高考不理想,我只能去读大专,从那时起,父母对我的前途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咨询了开连锁餐馆的亲戚,认为做厨师是理想务实的选择。十七岁的我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进入了一年花费需要十万的厨师学校。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学厨过程中,我丝毫不敢懈怠,学不好还自己躲起来偷偷练习。但日子一久,我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只是在被动完成任务,这不是我未来想从事的职业。
抵触的情绪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做菜时我频繁走神,有时还会头晕眼花,喘不上气。我计划着如何跟父母开口,从这份厌恶的工作中解脱,这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一次寒假,我在父母的要求下准备饭菜,故意表现得技术生疏。母亲忍不住质问原因,我趁机表达了内心的痛苦。“花了这么多钱,你想不上就不上了,你以为家里很有钱吗?”没等说完,母亲就打断我,父亲则在一旁保持沉默。
无法挣脱被规定的生活轨迹,我只能回校完成大专最后一年的学习。毕业后,我先后辗转于厦门、兰州和杭州,换过三家餐馆。我讨厌锅里溅出的油、冲起来的烟、高温的空气和狭小的厨房。厨房里来来往往的脚步急促,所有人都神经紧绷。困在厨房的日子让我感到无望。磕磕绊绊干了一年半后,我再也坚持不下去,最终决定辞职。
与其说我逃离的是一份不喜欢的工作,不如说是逃离父母无处不在的掌控欲。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对我严格要求。上学时,成绩是他们评判我的唯一标准,工作后,这个标准换成了薪水。稍有偏离预期,他们就会强制干预,连工作都要替我安排。默默服从了二十几年后,我迫切想改变现状,再不反抗,连结婚生子都会被安排。
2021年8月,我无意间刷到一则船员招聘,密密麻麻的行文中,“南极”两字瞬间抓住我的眼球,令我生出远离家乡的冲动。我想象着把自己丢进海里,在一片湛蓝中缩成一个无人在意的黑点,这让我感到无比放松。我决定了,无论干什么,先去南极,逃离这令人泄气的生活。
当渔船在一片轰鸣声中缓缓驶离岸边,眼看城市的建筑群逐渐变小、褪成灰色,最后被拉成一条直线,我发现自己对陆地毫不眷恋,甚至享受这种与现实生活切断联系的感觉。
02
逃离
能逃离现实,首先得益于忙碌的工作节奏。
在船上,我先被分配到厨房,后来又去冷冻室做搬运,忙碌时也参与绑船、挂包、编缆、捕网等工作。大家累得从不缺觉,船翻了也能睡着。每当轮到休息时间,我都累得睁不开眼,跌跌撞撞摸回宿舍,倒头就睡。我感激这份辛苦的工作,让我没时间再去想那些陆地上的烦心事。
渔船在几百平方米的海域来回作业,我们把渔网撒下去、固定好,几小时后再用机器打捞上来,一次能捞40吨虾,然后打包、装箱,搬往冷冻室。渔船实行六小时工作制,每工作六小时可以休息六小时。这是一份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半年下来,我从170斤瘦到125斤。
在高强度的压力下,与我同期上船的三个船员,工作了半个月就吵着要回家,三个月后才等来一艘货船,将他们捎回去。
图|船队日常作业
一艘小小的渔船,仿佛一个真空环境,很多社会规训都不复存在。船上的人际关系简单,大家上船的目的都很简单,有人为了躲避债务,有人只是想捞一笔快钱,我们很少关心讨论彼此的过去。我在这里肆意解放天性,喝酒、吹牛、赌牌、展示纹身,这些是我在陆地上从来不敢做的事情。
在南极,我有了与家人切断联系的正当借口——没网。很多次,我站在甲板上,望着南极海域茫茫一片,恍惚觉得天地之间只有自己一个人存在,逐渐感到心胸开阔、呼吸顺畅,心情也好起来。时间一久,我产生一种错觉:自己一出生就在这艘船上,而陆地上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我厌倦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与嘈杂的人群中穿梭,按部就班的工作令我兴趣索然,复杂的职场关系对我是一种折磨。我不具备任何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的品质,比如健谈、幽默、察言观色。从前去一些应酬的饭局,我总是张不开嘴说一些漂亮的恭维话,徒增现场尴尬的气氛。在陆地上,我需要费力地扮演一个能被社会接纳的人,这令我感到疲惫至极。
图|南极日落
为了挣脱内心的枷锁,我不止一次冲破社会规训,放任自己去做一些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事情,仿佛这样才能感受到活着的乐趣。
放弃成为一名厨师后,我曾独自前往新疆旅游,这种反叛给我带来了自由的快感。我尽可能去体验一些极限项目,滑雪、骑马、射箭、跳伞、徒步。仅一个月,就花光了一年的积蓄,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留下。我就没打算返程,而是在当地果园打零工,摘了三个月苹果,一天两百元。
父母在电话里责怪我不务正业,进一步刺激了我脱离正轨的冲动。我发现只要不联系家人,就能获得短暂的宁静和自由,摆脱畏畏缩缩的状态。我尝到了失联的甜头。
从新疆回来后,我闲在家里,找不到事做,母亲冲我大吼“养你还不如养条狗。”我冲到阳台,站在围栏上大哭,哭完冷静下来,看着脚下几十米的高空,有些错愕,我连死都不怕了吗?在家消沉了两个月后,我告诉自己必须离开。
一份去贵州六盘水山区支教的工作打动了我,父母却毫不掩饰对我的讽刺:“自己都挣不到几个钱,还想帮别人,哪个学生需要你这样的老师?”父母的态度,反倒令我产生了一丝快感:一定要去!
与之前几次的反叛不同,南极的工作因为有不低的报酬,并未遭到父母的反对。但我在意的并不是这份薪水,而是这遥远的无人之境,能让我暂时摆脱控制。父母远在万里之外,即使再想伸手,最多只能打个电话。
03
下船
然而,即使逃到再远的地方,桃花源仿佛也仅存在于想象之中。渔船的辛劳和南极的孤独,时间一长也很难抵御。
渔船顺着太平洋西岸一路向南,抵达南极,单程耗时两个月。前往南极的兴奋很快被生理的不适冲淡了。我没料到自己会严重地晕船。每逢渔船撞上大浪,房间里的东西都纷纷滚落,在地板上来回跳窜。人也站不稳,只感到头昏眼花,胃里翻江倒海,几天后体力就变得空虚。
2022年10月末,南极迎来极昼。两个月里,我所在的海域,白昼长达20个小时,太阳终日挂在头顶,白色的天光像火焰一样燎得人焦躁难安。我们的作息也变得紊乱,只能困了就睡,但睡觉时总会被门外的脚步声吵醒,昼夜和虚实都失去了界限。
图|狭小的宿舍
为了遵守南极公约,每年渔船只能在2至7月作业,剩下的七个月,我们待在船上无事可做。2022年7月,我第一次经历极夜,黑夜长达20个小时,这是渔船最清闲的一段时期,时间变得无限漫长。
无工可上的时候,我们都强迫自己睡觉,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醒来总是头疼。打发时间的方法有限,无非是喝酒赌牌。起初,面对同事们的多次邀请,我都拒绝了,这来自父母对我的告诫:任何上瘾的事都不能做。
我整天躺在宿舍读小说、看电影。直到把船长拷贝的50部电影看完了,自己带的小说也翻遍了。连续三天无事可做后,我决定做点什么转移注意力。我起身走到食堂,那天夜里赌牌输了五千块。
极昼白天还能拉上帘子,极夜是真让人着急。渔船被黑夜和涌动的海水吞没,透出点点微光,夜长得令人心慌。我站在甲板上,生怕海里出现庞然大物把自己拽下去,恐惧黯然滋长。
我曾渴望把自己抛向虚无,最终发现彻底的孤独令人难以忍受。在条件有限的南极,渔船渐渐成为一座与外界失联的孤岛,这对有社交需求的普通人来说很难适应。
整艘船只有食堂有网络,网费一个月100元,网速很慢,发消息总是延迟,一张图片需要三五分钟才能成功上传。打电话则需要卫星通话,100分钟200元钱。除了个别热恋中的船员,船上大多数人都不会使用这个功能。
我不愿和熟悉的亲人朋友联系,但无法完全做到切断社会连结,于是转而去社交平台上结识陌生人。坦白讲,谁不希望获得理解和认同呢?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更新南极的见闻,异域的风景引来一些网友围观,但我们的交谈仅止于聊一些新奇的经历,没人关心我的内心世界,我好像更孤独了。
一年过去了,南极对我已经不再具备最初的吸引力。现在的我,不再总去甲板上望着远方发呆。再新奇的事物,天天看也就那样。最极致的体验拥有一次就够了。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我对陆地的向往又回来了。
一次,渔船遭遇了一年里最猛烈的风暴,渔船在狂风巨浪中摇摇晃晃,物品在房间里飞来飞去。那一刻,我以为渔船要完蛋了,出于强烈的求生欲,我抓紧床边的栏杆,脚底却一直打滑。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整天。
图|风暴暂歇后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