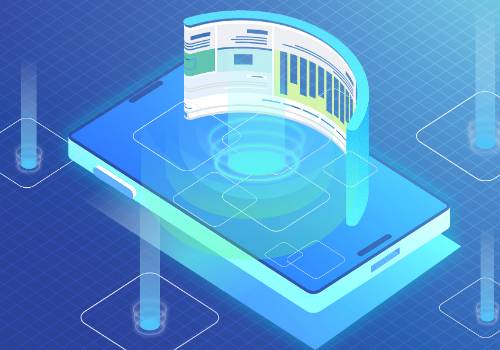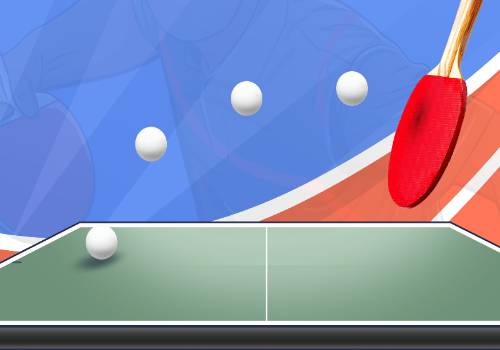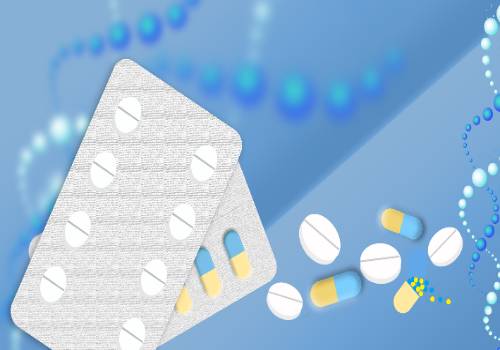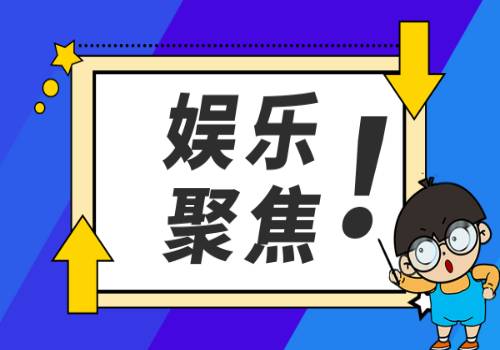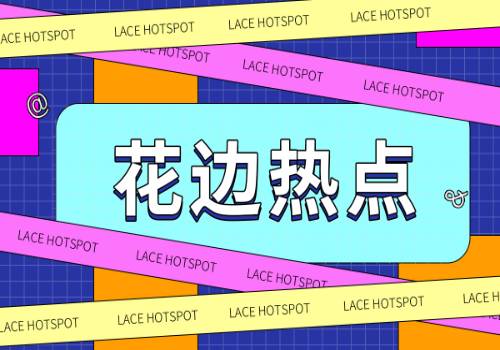失而复得
11月6日,一个天气阴郁的周日,在零上四度的寒冷里,北京马拉松重启。早上七点半,随着天安门广场前的鸣枪,三万名跑者挤满跑道,柏油路面被五彩的跑鞋占领,肌肉线条紧实而美丽的腿闪过,一种令人愉悦的喧嚣升腾起来。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失而复得。”跑者们这么形容站在起跑线上的心情。
2022北京马拉松起点©小崔
2020年和2021年,北京马拉松均因为疫情停办。这导致诞生于1981年的北马今年才算四十周年。10月3日,官方宣布启动报名,跑友们迅速开启了一场“自我矛盾”的挣扎。心理上,那是一种被本能压制住了的高兴和激动,在经历了长沙马拉松改为线上和无锡马拉松延期后,“北马真的能办吗?”“不站在起点线上我都不相信。”与此同时,朝阳公园、奥森、故宫墙根下,一场场长距离拉练被迅速组织起来,名头就是“备战北马”。
彤彤曾在2019年担任过官方配速员。她的想法代表着面对不确定时,跑者会如何选择:不管能不能办,先准备着,“我们都准备三年了,还差这三天吗,是吧?”直到确定将再次担任2022年北马的配速员,她才相信北马真的来了,如今,她只希望观众能多一些。
千万别小瞧来自陌生人的“加油”,跑者们说,跑崩的时候,路边群众的热情常让他们感到“走都对不起人家”。一位在崇礼越野赛中崩溃的跑者遇到了村里几位站路边看热闹的老乡,“为了面子也得跑几步”。在另一位跑者6年前崩溃的记忆里,至今留存的除了那种“怎么跑都跑不到头”的感觉,还有路边跳广场舞的大姐,以及补给站的人递过来的一块西瓜。当然,有时候观众也会起一些难忘的“副作用”,同样是这位跑者在广州马拉松跑崩时,看到路边的私人补给站提供西瓜,那一刻,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想吃西瓜,“你又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要,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跑。”他更难受了。没错,他跑马拉松时最爱吃的食物是西瓜。
©视觉中国
马拉松总长度42.195公里,而真正的考验在最后十公里,那是跑者们体力达到极限,最容易产生“撞墙”状态的阶段。简单来说,就是哪都疼,每根筋、每块肌肉都让人想哭,想死,想放弃。对于北京马拉松,在开启最后十公里前,还要先征服科荟桥——一段长达200米的上下坡。
位于北四环外,京藏高速上的科荟桥是北京几百座立交桥里最平平无奇的那一种:水泥色的桥身,绿色的护栏,桥头上立着蓝底白字的指示牌。有足足三年,科荟桥没能迎来它的高光时刻。6号上午,科荟桥再次迎来了彩色跑鞋和加油声。
已经到了在户外骑车会冻耳朵的季节,但寒冷没能驱散赛道旁的大批人群,也只有在北马这一天,你可以卯足全力、毫无顾忌地对着陌生人大喊,“加油!”一路都是如此。据跑者们说,人群没有往年那么热闹,但也足够让他们感到振奋。下了桥向右转,就向奥森公园,也就是终点进发了。还剩十公里处,一位大叔大喊,“还有十公里了!”到了剩余三公里处,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位小男孩。一位梳着齐刘海,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士在敲大军鼓,人人都在喊。一位路边的街道清洁人员也停下来,用冻红了的双手给跑者们鼓掌。
市民为马拉松参赛选手加油助威©视觉中国
相比之下,最后这段路上的跑者们显得有些生无可恋了。大批缺乏经验的跑者在和“撞墙期”作斗争。2014年,一位跑者下桥后没多久开始“撞墙”,还是那种感受,哪都疼,终于跑进奥森的时候,两行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疼哭了。
在生活尚未失序的时候,以上种种北马记忆远谈不上特殊,更别说世界广阔,各种各样精彩的赛事等着跑者们去挑战、去征服。但在当下,倒别有一番风味了。
比赛停办的两年里,在北马原定举办的这天,跑友们用脚守住这一天的秩序。他们沿着北马既定的路线或自己制定路线,在北京街头或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完42.195公里。就好像勤奋备考的学生从不因考试延期而懈怠。在没有马拉松的日子里,跑者们一直在奔跑,既是体能储备,又是肌肉记忆,更是一种仪式感的维持,所有的准备都是因为坚信,包括比赛在内,一切都有着“重启”的可能。在北马重启前后,我们与几位跑者聊了聊,他们有数次参与北马的老将,也有首次参加的新人(其中一位在北马停办的两年里,跑完了人生首场“虚拟马拉松”),还有的跑者为了备赛长期拉练,却落选中签,只好当一名合格的观众。
11月6日,这些幸运的跑者都站在了起跑线上,他们抱着一种隐隐的、热切的态度,既是因为两年期待终于成真,也是因为面前的42.195公里不止是一场比赛,而是也许、可能,未来将有更好生活的通路。他们想要失而复得。
人们首先爱上跑步,然后才爱上马拉松。后者意味着对身体和意志的极限挑战,但奔跑本身,在跑者们的讲述里,则更多出于甘之如饴的体验。在没有马拉松的日子里,我们的跑者没有停止奔跑,但并非是一种咬紧牙关的“备赛运动员”的姿态,反而是闲适大过痛苦,宁静大过紧张,用当下的话说,奔跑中自有心流,可以对抗焦虑、化解无力——每一个经历当下的人都明白,这有多重要。用一位跑者的比喻来说,跑步就是征服一个个有着不同形状的小怪兽,那是朝阳公园里由不同步道形成的路线图。带腿的,不带腿的,带尾巴的,胖头的,全长五公里的,十公里的。刚开始跑时,她还需要看手机画怪兽,现在,怪兽在她的心里。
跑步路线图©小崔
当北马重启,跑者们重新站在起跑线上,就像一次自我证明,证明三年中积攒的“心流”对抗痛苦的能力。
疫情前,33岁的程序员小崔有过一段四处疯狂比赛、追求成绩和速度的经历,疫情后,比赛少了,不再需要严格的训练计划,日复一日的佛系跑步才真正地融进了他的日常生活。
他很少乘坐交通工具通勤,十公里的路要么跑步要么骑车,到达办公室后“整个人觉得精力特别好”——要知道有多少人被通勤折磨得死去活来。家住奥森附近的他绝对称得上北四五环活地图。不需要使用社交媒体,他就能在跑步中选定周日可以拿上一张毯子带家人去野餐的理想绿地。
如讲述私藏品一般,他分享自己喜爱的两条跑步路线。一条是奥森南园挨着北五环的平坦小路,人少,没有红绿灯,早春的花在这里悄悄开放,只给他独赏。有次他在这条长度1.7公里的路上独自跑了两个小时,来回反复。另一条是绕着鸟巢的封闭道路,2.2公里,路宽,早上人少,迎着太阳跑,“越跑越暖和,特别舒服。”
北马宣布重启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中签了。这是他今年的第一场比赛。
居住在学清路和清华东路的Linda今年首次参加北马,她很少跑长距离,但相当持之以恒。每天早上六点十五分,Linda和丈夫起床,她把孩子早餐准备好,6点半前两人出门跑步五公里,“精神被激活了”,七点回来送孩子上学,然后上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今年1700公里的跑量就是证明。
Linda向我描述她眼中的附近,那种曾被学者项飙哀叹我们失去的附近,“有时我们在河边跑,从数九天看着树秃秃的,然后吐嫩芽,变成那种黄绿色,变成翠绿色,变成墨绿色,然后秋天来了一阵风,那个树叶哗哗哗哗在你眼前落,早晨的太阳打到树上,投到你面前,那种光影的感觉,瞬间就感觉生活很美好。冬天有一次刚下雪,天还挺冷,雪还没化,都挂在树上,你觉得一年又过去了……你天天开车,等红绿灯着急上班,你不会注意到的。但是你要是跑着的时候,那个风景像慢镜头一样,就特别美。”
疫情当下,她觉得跑步是回归一种简单。“可能我们在慢慢适应这种疫情啊什么的。只要穿一双跑鞋我就跑去了,只要不封控在家,这项工作你都能做,对不对?”
如果说跑步对于有的跑者是一种简单生活的象征,那么对于笑笑来说,则是崩塌后的重建,重新超越自己。
二十六七岁那几年,年轻的笑笑狂热地爱着跑步,上海、成都、无锡、香港的城市路面上都曾有她的足迹。她的PB是在名古屋女子马拉松创造的,4小时25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很多选手的男朋友或丈夫会在路边cosplay动漫人物为跑者加油。冲过终点后,西装革履的男模为她送上缀着白色蝴蝶结的蓝绿色纸盒,里面是一条Tiffany的项链。2017年,她的项链是一朵银色的玫瑰花。那时她觉得靠自己的双脚,而不是钱财或他人的馈赠得到一条Tiffany,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名古屋女子马拉松收到的蒂芙尼项链笑笑
再后来是2019年,女儿出生了。2020年疫情来临时,她还在哺乳期。与其说是疫情,倒不如说是孩子把她困在家里。她把那两年的育儿形容为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很无聊,日复一日,但是你又必须得去坚持。”
产后三个月,一次喂奶过后,她把孩子“扔”给丈夫,穿上陪伴了自己五年的跑鞋,下楼重启跑步。立秋过了,树木还翠绿,但空气中已有一丝凉意,北京最美的季节即将来临,而迎接她的是每跑一步的耻骨痛,以及消失的腹部核心,“你的屁股往下坠,胸也往下坠,胳膊都是囔囔肉,腿也是囔囔肉,脸也是松松垮垮的,所有的肌肉都没了。”
对于疼痛,“忍”。当象征着年轻和力量的东西消失后,意志是她仅剩的武器。产后121天,再次完成十公里跑后,她在朋友圈里写,“技术在灵魂面前必输。”这时她的耻骨痛仍未消除。而要到一年后哺乳期差不多结束时,她才会重新感受到核心的力量。
2020年8月的崇礼168国际超级越野赛是她产后完成的第一场比赛。意志之外,完赛还得益于朋友和家人给一位哺乳期母亲的巨大支持。朋友把她开车送到起点处,抵达第二个打卡点之前,涨奶让她的乳房开始疼痛,朋友和丈夫带着孩子在那里等待,让她给孩子喂了一次奶。最后的十二公里,疼痛蔓延到全身,丈夫背着孩子陪她一起走,她发来的一张照片里,婴孩白嫩的小胳膊搭在父亲的肩膀上。快抵达终点时,才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被放了下来。她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穿着粉色的上衣和白色斑点裤子,用还不太稳健的步伐牵着母亲的手走过了终点。
她还差产后的第一场城市马拉松来证明自己,昨天,她站在了北马的起跑线前。
笑笑牵着孩子的手走过终点©笑笑
即使我们的生活如此脆弱,如此不完美,但能在一个阴天的周末跑完42.195公里,仍然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