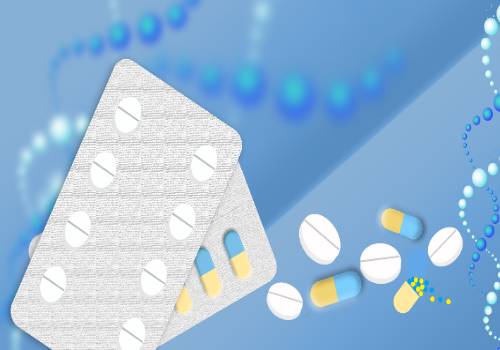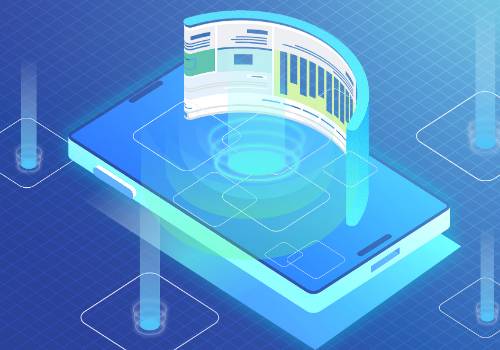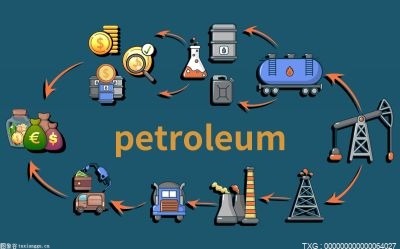一个未脱敏的女孩
 【资料图】
【资料图】
落地尘
老师们在把班上的特殊孩子——特别有个性、有特殊经历、有别样喜好、有另类习惯的个别孩子——推荐给我的时候,总是期待问题得到解决,并且最好是马上出效果,立竿见影。这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没有哪一位心理治疗师有瞬间起效的灵丹妙药,何况这些孩子的问题已经滋长了一些时日。我还要花时间去了解他们的感受、行为模式,去深挖浮现出来的表象所隐藏的东西。那么要想脱离有问题的孩子带来的困扰——他们各有各的问题——这不是单独某一个方面能下结论的,多半是综合因素的作用,涉及老师、家长、同伴。
在朋友圈看到过一篇推文《我看山东卫视的超级语文课》,很赞成里面的观点:眼中有教材有学生,心中有生命有生活,足以抵过“新理念”的千军万马!在动不动是“大单元”整合,“任务群”推进,七七八八、轰轰烈烈的所谓理念狂轰滥炸的时候,回到朴实,回归自然。
其实心理帮助或者叫心灵关爱也是一样的道理。面对不同,没法逃避,只能接受,然后尽可能去改变。没有谁有通天的本领。2021年9月开始,我用一年时间参加了一个心理督导班,今年10月即将毕业。学习了舞动疗法、绘画投射、NRC、叙事疗法、箱庭、萨提亚等各种技巧,在深入了解督导班学友们对专业与工作的热爱之后,回顾做白雪公主沙盘的她,闹脾气自我放假的另一个她,厌学逃避的他……我认识到,比起道理或者技巧,咨询师或者教师最有力量的事是放下咨询师或者教师的角色,真诚地去面对真实的生命真实的孩子,去看见,去聆听,去感知,去信任。
这需要勇气。这也很冒险。或许我改变不了问题,但我可以让周围的人改变对他与她的态度。有些东西不能变,但是改变确实发生了。面对问题,不是抱怨而是直面问题,改变真的就已经发生了。
今天我想写写她,一个羸弱的女孩。
学校笑融融心理成长中心刚成立的时候,G老师就告诉我,在她班上有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希望我能帮帮她。G老师告诉我,她会无休止地在课堂上大哭,发脾气,义正辞严地警告无效,轻声细语地安慰无效,严重影响教学的正常进行。她与家长沟通过好几次,家长总说:“是的,我们知道,她就是玻璃心。”
从一年级起,G老师已经当了那个班三年的班主任了。她还教科学课。她对我说起的时候愁眉苦脸,显然她对那个孩子付出了大把的心血却仍然不见起色。G把她归结为问题儿童一类。
我把她列入清单,把她的班级姓名写在我办公桌桌面上的即时贴上。排在她前面的还有三位孩子。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班级。那是我至少两周的额外工作,或者叫第三份工作。我计划在星期五做一个团体沙盘,借助玩具、沙子让来自不同群体的孩子回归游戏世界,敞开心扉,回归真实的自我。
我想借助沙盘观察他们的个性。
孩子的内心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沙子可以帮她“说话”,在沙盘游戏中泄露的“天机”给咨询师搭建了游向她心灵世界的渡船。
那天,即时贴上的四位孩子与我班上的另外四名孩子做了团体沙盘。
八个孩子有男有女,她是个头最弱小的一个,脸庞狭长,躯体羸弱,头发枯黄,身着浅蓝的短袖校服,裸露的手臂让人联想到螳螂。除了最开始我登记时她报告了班级姓名,自始至终没有再说一个字。她的嗓子很健康,不洪亮,属于女孩子的尖细。
那天做沙盘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在她的表现上。八个人排成一队,一轮一轮地挨序从架子上拿玩具,摆放在沙箱里,看不出她的悲喜。除了不说话,不用招呼,她很顺从地按照指令来。一个正常的很乖巧的女孩子,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G老师问到,我如实回答我的感受:一个正常的很乖巧的女孩子。我的答案显然让G老师很失望。当然我理解她,她所经历的远比我短暂的一个小时的观察更为复杂。她皱着眉头,不满意我没有站在她的立场。
我的感受需不需要服从G的结论呢?一个麻烦的孩子。她的结论里藏着认识她的线索。她的教室就离我办公室不远,我们在同一楼层。我一直没有去认识她,就是不想受先入为主的结论干扰。我希望她遇见我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带着偏见或者张开双臂接纳她,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我准备好应付许多无法避免的挑战。我喜欢挑战。
沙盘过后,不知道是星期几,上午还是下午,我在办公室改作业,一起在办公室的有好几位同事。G老师在教室里上课。办公室原本很安静。突然,有同事轻声说:“G老师班上的那一个又干嘛了?”她的语音里有同情,有无奈。
果然,那间教室里是有尖锐的孩子的啼哭声,像被蝉声扰乱了宁静的夏日早晨。我的第一反应是:机会来了。我不假思索地冲出办公室,来到她的教室门口。教室里的情景很糟糕,三十几个孩子,各坐一凳,排成六排六列。她坐在第二列第四排张着嘴哇哇大哭,像被忽视的婴儿,哭声也像被惊吓的婴儿,尖叫性的痛哭。G老师对此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站在讲台上讲着题,侧身面对学生,一手指着板书。其他学生也若无其事地看着黑板。我出现在门口,除了她,所有人都扭过头看着我。
她在大声啼哭,老师在讲课,同学们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就是这样。也无法想象这样被严重干扰的课堂教学会对每一位孩子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惊讶着奇怪的课堂。他们惊讶着我的唐突。
我觉得场面好笑,在门口站立了几秒,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向她走去。我把她从座位上轻轻拉起来,牵着她的手走出教室。在办公室,我找了一把椅子,让她挨着我坐下,看我改作业。
“有哪里写错了告诉我啊,我总是会看错。”我让她做我的眼睛,盯着我翻开的一本本作业。事实上,从我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那一刻起,她的哭声就戛然而止。此刻我也看清了,她的脸上根本没有泪珠。她的啼哭是干嚎。但是她确实很着急很痛苦,眉骨涨红起来,像在桌角被狠狠磕碰了。
我故意漏掉作业本上写错的字。她用手指了指,我故意自责:“看我这么不仔细,老师也有不仔细的时候。”我扭头看她,她已经平静下来,不过并不回答我的话。
“告诉我,为什么哭?”我想知道原因。她抿着嘴,没有回答我的意思。
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语文老师H也在办公室,就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也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刚才发生的一切。我认为他习以为常,见惯不惊。
“不想对我说是吗?H老师呢?愿意告诉他吗?”我主动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又是怎么了嘛?”H老师很勉强很无奈。
她还是抿着嘴,不害怕,也看不出来伤心和着急。
她看着我,不停指出错误之处。我表扬她作业一定认真仔细。不一会儿,作业都改完了,也到了下课时间。
总让她陪我坐在办公室也不是办法,我叫她回到教室里去。
G老师倒是很关切。她告诉我她当时就说了一句:“把……告诉你的家长,她就大哭。”G老师说的把什么告诉她的家长我忘了。我听出来那只是警告,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更像在威胁。
G老师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人,做什么事都是中规中矩。我可以想象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是如何一本正经。“我就说了一句”,显然她不认为她的话有什么过错。
G老师是很善良的人,但她忘了她是一个未脱敏的孩子,或者潜意识里她也并非要故意激发她的恐惧,我敢保证,她并没有恶意。
未脱敏是她的体育老师告诉我的,说她在体育课上什么原因整节课躲在厕所里不出来。未脱敏的孩子容易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很情绪化,在群体关系中,常常感到委屈、焦虑,甚至一言不合就会哭。严重的孩子甚至会一言不合就动手打起来。
从体育老师和G老师的描述来看,她符合那些特征。
人际未脱敏的孩子不能遵照大人的愿望去处理好一切与人打交道的事。一句平平常常的话、甚至一个无关紧要的眼神儿他们也总是会多想。在口欲期,家长保护过度,与陌生环境打交道过少会影响后面的适应顺畅,通俗说来,就是羞怯、胆小、紧张、焦虑、恐惧,缺乏安全感。
这是能够改变的。而我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她摆脱恐惧感,让她体验到关爱。同时要做的是让G老师找到和她相处的方式。我要帮助的有两个人,她,还有G老师。
群体里得有亲近的人。具体的亲近的人越多,集体向心力就越强。G老师班级的座位排列是六列六排,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没有同桌,像三十六座孤岛。一般考室就是那样布置,很多班级在临近考试的复习阶段也会这样安排,为的是不要互相干扰。如果孩子到学校仅仅为了考试,这样的彼此联系松散的座位也无可厚非,可是他们到学校就仅仅是学知识对付考试么?如果是那样,回忆起童年的学校将会不会增加他们的遗憾?他们本应该拥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包括同桌的他,或同桌的她。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权力。
我把想法告诉G老师,半信半疑的,一声令下,她将临近教室门口的两个小组的桌子靠拢,一半变化,一半照旧。那天早晨,在路过她的教室时,我很惊喜。这对她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预想着将要发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她有一个物理意义的亲密同桌,继而会发展成心理意义的亲密朋友。这是关键。
预想变成了现实。有一天,在我办公室楼下,两个蹲在花台边的头碰头的女孩突然站起来,手牵手推开玻璃门,蹦蹦跳跳地跑进了多功能室外面的门厅处。她们无拘无束,毫无戒备。其中一张面孔好熟悉,走了几步再回头,果然是她。
我对她是充满希望的。我不认为她不正常。
又是一天,在办公室,我又听到了她似受到惊吓的尖细啼哭。这一次,她就近在咫尺,正颤抖着身子站在G老师面前接受训诫。G老师很生气,眉毛皱成两股绳,言语冷峻,看着她的眼神里充满失望。这次,是她动手打人了。
我走过去,蹲下身子一把抱住她。她立即停止了啼哭。
是课后延时服务时间,我陪伴了她一节课。我牵着她的手敲开一间间陌生的教室,在教室过道里来回走动。在我的教授下,她接受不同班级的群体审视,她大方地问候“大家好”,她做自我介绍“我是……”。她很愿意做那些事。她不是被定义的“未脱敏”。
她很正常。
“改变看她的眼神,”我对G老师说,斟酌着字句,“改变与她对话的方式,妥协一下,互相迁就……”我把她牵回到办公室,像劝解两个闹别扭的孩子,把她的手放在G老师的手心里,我说:“握住她,感受彼此的体温。”开始她们都不自在,后来,G老师把她紧紧抱住了,她们都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得说明一下,G老师还是未婚女孩。但我看到,她开始沉思孩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