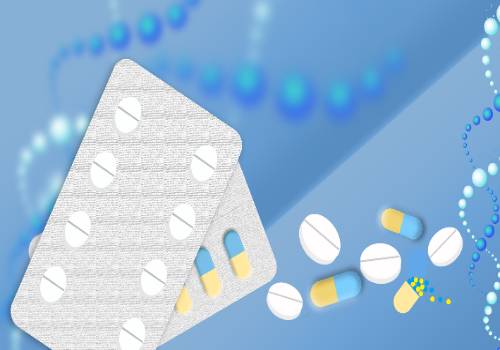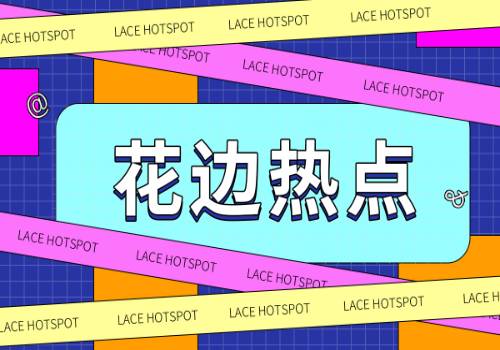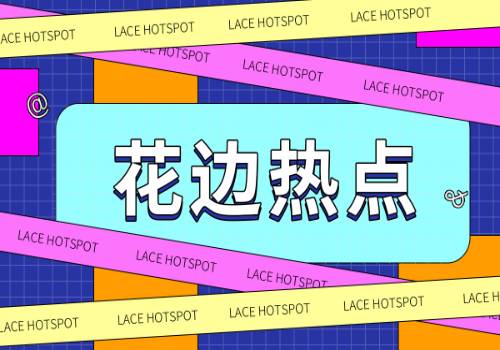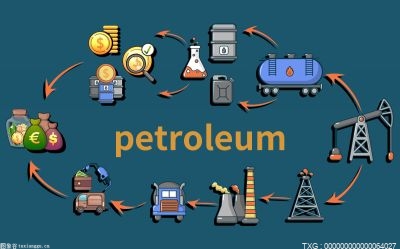《明朝果然很有料》-二百十六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刘健干了点什么事呢?
说起来干了很多,财政、军事、等等,刘健屡有进言。史载刘健“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为他赢得了贤相的名声。
持正敢言是值得嘉许的,疗效就另说了。
前面提到过,朱佑樘的鸡血期大致在弘治七八年的时候就结束了,此后他开始进入漫长的倦怠期。
说他倦怠其实不对,至少表面上不全对。看起来朱佑樘依然是个纳谏如流的君主。有点脾气的皇帝,不同意的奏章会驳回,会留中不发,朱佑樘基本不见这样的记载。无论大臣提什么意见,只要不触及到他的底线,随处可见他“纳之”、“嘉纳”、“嘉纳之”。
纳归纳,办不办是另一回事。刘健成为内阁首辅已是弘治十一年,早就过了他老人家早年振作有为、裁撤弊政的鸡血时期。从中期开始,弘治皇帝就开始对国事表现得不那么感兴趣,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越了晚年的朱见深。
比如宪宗皇帝虽不喜单独召见大臣,也不喜欢听人讲经,至少门面功夫还是装点得很好,常朝、经筵一个不落。
朱佑樘就有点不讲究了,一个月三次的经筵被改为一年几次不说,连常朝也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大臣们的奏章他同意归同意,就是拖着不办,你能拿我怎样(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
另一方面,要找出他不那么虚心接受批评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在对待张皇后一家的问题上。
我们要表扬朱佑樘同志践行一夫一妻制的先行者精神,也要批评弘治皇帝对外戚的纵容。总体来说明朝的外戚算是比较安分的,要在这么多家外戚里挑个闹腾得凶的,那就得排到弘治一朝。
朱佑樘只有一个张皇后,最受恩宠的外戚自然就是张家。
朱见深再宠爱万贵妃,也不过是授予万喜等人锦衣卫的虚职。朱佑樘直接就将张皇后父亲和两个兄弟封为侯爵,就连国舅张鹤龄的几个亲戚,也一并提拔为锦衣卫百户。
有了这份荣宠,张家兄弟不满足于做些开店设肄、败坏盐课的非法生意,还开始欺压百姓、夺民田庐。甚至太皇太后周氏娘家头上他们也敢动土,为了争田,周、张两家积怨越来越深。弘治九年,寿宁侯张鹤龄与长宁伯周彧因琐事纷争,聚众斗殴,一时轰动京城。
张家民愤越来越大,大臣开始不断上奏弹劾。由于张皇后的关系,朱佑樘不忍处罚两位舅爷,按他的性格,也不能一意孤行斥退大臣,于是在外戚问题上,弘治一朝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画风。
一次,司礼太监萧敬等宦官,和刑部侍郎屠勋等朝官一起,处置了二张兄弟侵占民田的家奴。张皇后听闻此事大怒,叱骂萧敬说:外面的朝官我管不了,你们太监本是家奴,也敢欺到头上?
朱佑樘在旁听到,也是怒不可遏,忍不住跟着妻子高声叱骂萧敬等人。
可一回头,等张皇后离开,朱佑樘便召来他们打招呼,说我方才是不得己,不能伤了皇后心,你们就当这事没发生过。赏你们每人五十两银子,这事别传到外面。
后来不知是谁嘴碎,事情终究还是传到外头去了,朱佑樘的一百两白银算打了水漂。
张家不知收敛,户部主事李梦阳忍无可忍,直言上书,写了有名的《应诏指陈疏》,直指张鹤龄“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夺人田土,拆人房屋,虏人子女,要截商货,占种盐课,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等诸多罪行。
如此指控相当于与张家刺刀见红,张鹤龄和他老母金夫人在皇帝面前泣诉不止,要求处死李梦阳。
朱佑樘并不糊涂,他明白李梦阳指控属实。他做不出迫害忠良那种事,可也不好拂了岳母和小舅子的面子。想来想去只好发扬和稀泥精神,一边切责张鹤龄,一边又将李梦阳下狱让张家解气,过几天随便找个理由将他释放。
这位李梦阳是弘治七年进士,著名的文坛复古派前七子领袖人物,善工书法,精于古文词。当时文坛魁首首推李东阳,他以“馆阁体”领导全国文坛。后起之秀李梦阳偏不服,他嘲笑这种文体拘恭有余不足,李梦阳提倡写文章要以秦汉文章为范本,写诗要以盛唐诗体为榜样,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李梦阳文章写得好,同时还是个暴脾气。没打到老虎还被反咬一口,即使获释他也怒不可遏。
皇上不给我做主?好办!我自己解决!
李主事捋起袖子,找了两块板砖就蹲守在在张鹤龄下班必经之路。看到张国舅出现,李梦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出,举起板砖就拍了上去
张国舅哪知这个冤家如此手黑,措不及防,两颗牙齿当场不翼而飞。
更离奇的是事后,这位堂堂寿宁侯不知是心虚,还是怕了凶神恶煞的李梦阳,竟然不敢计较。
不过,对外臣有所顾忌,对内臣,张家兄弟就没那么客气。弘治对小舅子们的一再纵容,最终引发了一桩命案。
一回张家哥俩进宫参加晚宴,朱佑樘起身方便,这两人胆大包天,抓过皇上的帽子就套在了自己头上。
别说小舅子,亲儿子都不敢干这事,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这绝对是大逆不道。
朱佑樘的长随太监文鼎大怒,手持金瓜上前欲击打张氏兄弟,被当时另外一名受到宠信的太监李广阻止。
文鼎随后便以二张以“无人臣礼”为由,将此事上奏,要求朱佑樘处罚。谁料皇帝不但不处罚二张兄弟,反而让锦衣卫将文鼎下狱,张皇后更指使李广将文鼎杖杀于狱中。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满朝官员上书弹劾张氏兄弟,朱佑樘实在装不下去了,只能说了实话:朕只有这一门亲,再不必来说。
后来朱佑樘才明白文鼎被冤杀,颇有悔意,命以礼收葬,并亲自为他写下悼词。但也仅此而已,张皇后和她兄弟并未受到惩罚。
骄纵外戚是弘治一朝无可辩驳的失政。可以说,朱佑樘既爱张皇后,又怕张皇后。为了让皇后高兴,他总是尽可能满足张家人的欲望,宁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也不忍指责爱妻;身为皇帝他又不能不考虑国计民生,面对大臣责难,不得不连哄带骗处处敷衍。
一个皇帝活得这样也是挺累的。弘治十八年,朱佑樘因北方旱灾而祈祷求雨时偶感风寒,服药后鼻血不止,竟致不治,驾崩于乾清宫,得年仅三十六岁。
后世给了朱佑樘极高的评价,将他奉为不世出的明君。万历年间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将他的统治称为“弘治中兴”。
以我看来,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朱佑樘虽不是昏庸之辈,但也决非中兴明主,他能博得后人如此美誉,实在值得深思。
文官们对他很满意,所以把中兴的标准被放低了。表面的稳定终究不能掩盖社会矛盾的持续积累。到了弘治末年,已是国库空虚、边防废弛、流民日增、“民穷财尽”。就算不说是烂摊子,也跟所谓的中兴盛世半点搭不上关系。
如果真要说中兴,那也应该和他老子连起来说,叫“成弘中兴”才对。
总体来说,朱佑樘的统治并没有超越父亲朱见深,在不少地方甚至还有倒退。比如河套、财政,还有让他烦心不已的外戚问题。
比较而言,弘治皇帝是位中规中矩的守成皇帝,所谓“勤政亲贤”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复杂的社会矛盾,危机正在潜滋暗长。
不管官方文件对他如何定性,那也都是别人的意思,朱佑樘自己的一番遗言,才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
弥留之际,他把太子朱厚照和几位大臣叫到床前,叮嘱道:
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乃得此疾,殆不能兴,故与先生们相见。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朕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玩。凡天下事,先生们多费心,我知道。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十日成婚。至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东宫,今十五岁矣,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礼部举行。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们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
这段遗言里,关于他十八年的执政内容只有短短两句,绝大多数篇幅都留给了家人。其中提到的两个日期,都是关于妻儿,何年何日成婚,哪年哪月得子,记得清清楚楚。
人之将死,什么江山社稷,什么后世评价,都变得不重要了,只有家人才是他最大的慰藉与牵挂,这点皇帝也与常人无异。
知子莫若父,这是一个父亲临终前的谆谆教诲。朱佑樘明白做皇帝的难处,更明白这个儿子的性情。
既然你注定要成为皇帝,那么,就算你不能当个模范皇帝,也别当个昏君。
记住,做个好人就成。
在一部电视剧中,又将弘治皇帝弥留时的情境演绎了一番,看得出编剧是有深厚功底的。剧中,判官前来勾魂,与朱佑樘进行了如此一番对话:
判官:弘治皇帝,再看一眼你的儿子吧。这一走,就再也见不着了。
朱佑樘:不用挂心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判官:朱佑樘,你只活了三十六年,不觉得忒短了点么?你的儿子朱厚照,能不能治理好大明朝?
朱佑樘:这也不重要。跨过这生死线,我明白了,江山是主,人是客。我的儿子朱厚照,他过得快不快活,才是最重要的。
判官:那我来告诉你,你的儿子会活得比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快活。
未完待续=
本专栏是一部明朝兴亡的完整内容,从元末讲到明末,以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将持续更新,不少于100万字,定价将随篇幅增加而相应提高。
本书目前已与出版社签约,完成后将出版实体书,对明朝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购买电子版。作者已出版《南明那段日子》实体书,各大平台已上架,相关内容也以专栏形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