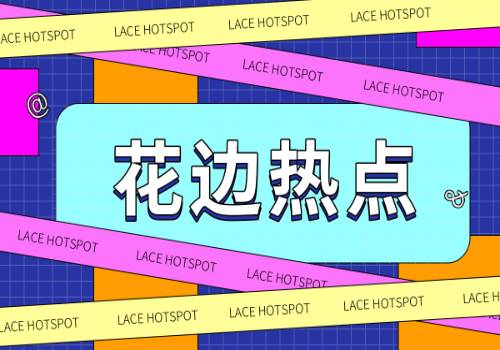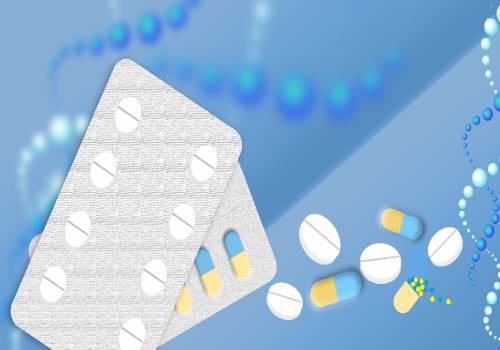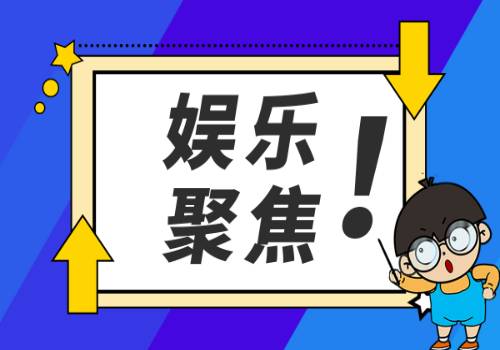1281年第2次远征日本后,元朝首先处理了战后诸项事宜,如战争损失、战况报告等。在对远征相关机构和人事进行整顿时,征东行省也暂时废止。高丽南部的沿海地区需要随时做好准备,以应对日本的反攻。据报告,1282年正月间,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金州,曾发生数起日本掠夺事件。不过,1282年开始至1283年,征东行省重新启动,开始筹备第3次远征,在中国江南和高丽,建造战舰、补充兵员、配置兵器、积蓄军粮等。高丽国王以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驸马的身份,比以前担负更大的责任,落实各项措施。当然,高丽那边也向元朝派遣使者,揣测元朝的真实意图,并尽可能力图减轻高丽的战争负担。几乎与元朝征日的同时,唆都等人也远征占城,但此后的进展并不顺利。此外,为了远征日本,元朝也曾试图借用重罪囚犯。于是,元朝陷入东方、南方两面作战的窘境,昂吉儿、崔彧、田忠良等人自然对远征日本计划提出反对或消极意见。普陀山僧如智提出遣使日本的方案即在此时。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在《元史》等元史史料中,并没有直接记载这一时期如智出使日本的情况,或许这次遣使最终并未成行,仅仅在记述此后王积翁、一宁一山出使日本情况时,对第9次日本遣使略有述及。在瑞溪周凤(1392—1473)《善邻国宝记》中收录有愚溪如智《接待庵记》这一珍贵史料。该史料分为前段和后段,前段包括至元二十年(癸未)八月如智奉旨与提举官王君治一起前往倭国始末的一系列记录,同时也包括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四月依旧奉旨与王积翁一起前往倭国的记录。前段结尾处注明该记录完成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
关于如智、王君治出使日本一事,池内宏曾有相关研究,其中提到“他们历经八个月时间,在海上逗留了太久。或许是故意在海上久做停留,之后王君治表示不想再出使日本”。史料并没有说明王君治究竟为何人或出任何种提举官,同时也没有史料表明王君治的正使身份。但是,仅据《接待庵记》后段的记载可知,提供此次遣使契机的人正是如智本人。《接待庵记》后段收录了如智携带的《宣谕日本国诏》:又记《宣谕日本国诏》,文曰:“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日本国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觐,朕亦命使相报,已有定言,想置于汝心而不(志)[忘]也。顷因信使执而不返,我是以有舟师进问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彼辄不交一语而固拒王师。据彼已尝抗敌,于理不宜遣使。兹有补陀禅寺长老如智等陈奏,‘若复兴师致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赍奉圣旨宣谕,则必多救生灵也,彼当自省,恳心(皈)[归]附。’准(奉)[奏]。今遣长老如智、提举王君治,奉诏往彼。夫和好之外,无余善焉;战争之外,无余恶焉。果能审此归顺,即同去使来朝。所以谕乎彼者,朕其祸福之变,天命识之。故诏示,想宜知悉。对于上述诏书,池内宏推测“可能并非原文”,并将诏书中“准奉”一句理解为“彼当自省,恳心归附准奉”。该诏书与第一次(第二次)遣使时大蒙古国皇帝致日本国王的国书相比,确实给人过于简短的印象。但是,笔者拟通过仅见于该诏书中的信息,来研究这次遣使的性质。首先要考虑的是原文中的“准奉”和“准奏”,究竟是诏书本身有误还是誊写时致误。王勇翻译该诏书为:“准奏,今遣如智长老和提举王君治。”除此之外,笔者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译法。
接下来,笔者拟通过“准奉”和“准奏”的用例进一步加以探讨。关于元代的“准奉”,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以下略称《元典章》)中有以下两个例子:
(1)至大元年......本台(行御史台)别无准奉明文,无所遵守。(《元典章》一二《吏部卷六·又·随路岁贡儒吏》)
(2)至元六年正月十七日,准奉右三部符文该。(《元典章》五七)
在上述两例中,“准奉”的含义均指某官司接受其上级官司的文书。在明朝史籍中,则有以下用例:
(1)臣等各准奉各该衙门关札。(《名臣经济录》卷三五《题为修饬武备以防不虞事》)
(2)臣等各准奉本衙门关札,署管后湖黄册。(《张庄僖文集》卷二《修理册库疏》)
(3)案验各准奉部院咨札,俱行该司会议。(《张庄僖文集》卷三《乞处补禄粮疏》)
上述3例中的“准奉”,均为接收文书之意。在宋代史籍中,亦有如下例子:
(1)所附到郑亿年申状,寻具奏闻,准奉圣旨,为已经放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八)
(2)西南北两路都统府差萧愈等赍到文字,准奉诏旨招谕者。(《大金吊伐录》卷四《辽主耶律延禧降表》)
(3)有诏,许存宗社,不害生灵,准奉太后戒命,举国内属。(《平宋录》卷下)
(4)如某粗修封管,准奉诏条,空竭愚驽,讵施方略,洎投恢网,益詟威灵。(《文恭集》卷三四《谢获群贼奖谕海用启》)
上述4例中的“准奉”,则指接受皇帝或南宋末谢太后等与皇帝平级的人的命令。此外,“准奏”一词多次出现在具有元朝法律文书集成性质的《元典章》中,例如:
(1)中统五年八月囗日,钦奉圣旨:
中书省奏“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
乞亦正名”事。准奏。可称中都路,其府号大兴。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元典章》一《诏令卷一·建国都诏》)
(2)至元四年十月,钦奉圣旨:“据中书省奏:‘管民官已行迁转,若是承袭,有碍迁转体例。今参议到职官自一品至七品承荫叙用条画,乞颁行’事。准奏。仰照依下项条画施行。”(《元典章》二二《户部卷八·榷茶运司条画》)
上引2例虽然内容简短,却是元代最常见的皇帝圣旨文书形式,其上奏主体、上奏文长短和事例的时期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某官司上奏皇帝后,针对这一上奏,皇帝采用“准奏”这一常套句型表示同意。“准奏”二字之后一般有皇帝的指示,但没有必要很长。于是,“皇帝圣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诏”体,蒙古语则表示为“Jarlig”(圣言),其本身具有法律效力。换言之,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传达,只要皇帝的旨意(包括臣下的上奏和皇帝的裁决)以圣旨形式记录下来,均是有效的,同时也是重要的。由此可见,前文中提到的《宣谕日本国诏》,即使篇幅短小,也是一通名副其实的诏书。如前文所示,笔者认为《宣谕日本国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这个皇帝圣旨是写给日本国王的诏书,简要叙述了“元朝对日本外交的过程”,并且指出根据两国交涉过程以及武力侵略的理由,元朝原没有必要向日本派遣使者。笔者对这一部分内容存疑,后面将加以讨论。第二部分为“如智等人上奏”。如智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和风土人情非常期待,于是自己提出要出使日本,坚信可以使日本归附元朝。第三部分为“对陈奏的许可以及如智、王君治的任命”。这一部分明确指出元朝想与日本修好,若日本同意归顺,则派遣使者随元朝使者一起返朝复命。与第一次(第二次)遣使甚至是第4次遣使时的国书相比,该诏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使用武力等压迫性言论,认为福祸由天注定,也有观察日本方面对策的倾向。元朝对日本外交态度的这种转变,无疑是因为元朝对日本的第二次远征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是,诏书中提到的祸福转化的含义非常微妙,暗示了若日本归顺元朝则为福,悖逆便是祸。这对于镰仓幕府来说,可能需要提高警戒,因为这并非简单的得失问题,而是事关日本存亡的重大问题。
关于第一部分“元朝对日本外交的过程”,首先存疑的问题是,因为日本遣使入朝拜见皇帝(遣使入觐),皇帝也命令使者向日本作出回报(命使相报)。根据有限的先行研究成果可知,这种历史过程难以考证。但是,若根据世祖的各种言论来分析这种可能性的话,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种情况。最有力的证据是第5、6次遣使,即赵良弼出使日本的情况。至元七年(1270),作为秘书监的赵良弼接到了出使日本的命令。当时的国书被收录在《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至元(六)[七]年十二月条中。关于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问题,第4次遣使时,大蒙古国中书省颁布的国书(收录于《异国出契》)中有“以战舸万艘径压王城”。与这种描述相比,赵良弼此次携带的国书措辞较委婉,回到最初的国书措辞方式。
至元八年(文永八年、1271)九月,赵良弼和日本人弥四郎一起抵达九州。赵良弼主张应该先面见朝廷或幕府等日本方面主政者,然后把国书转交日本。至元九年二月,赵良弼让其心腹、书状官张铎带领弥四郎等12名日本使者,经由高丽,返回元朝都城。元朝当时对日本使者的真实身份存有疑虑,也可理解为元朝怀疑这些使者前来大都的目的是刺探元朝国情。于是,元廷不仅没有宴请使者,还让他们与张铎、高丽随行者等人一起回国。在此期间,高丽国王接到元世祖的旨意,将其写给日本国王的国书送至日本。在日本时,弥四郎等使者尽力配合赵良弼的工作。尽管当时的元朝和高丽仍然心存疑虑,但也给予日本使者该有的待遇。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日本很有可能已经知道元朝的疑虑。赵良弼出使日本时,金有成被任命为书状官一同前往,据史料记载“日本承命,遣使朝元”。此外,在《善邻国宝记》卷上,文永八年辛未、咸淳八(七)年、至元八年条中,有如下记载:“日本遣使如元报聘。《元史》曰:日本始遣弥四郎者入朝,帝宴劳遣之。”该史料引用了《元史·日本传》的内容。作为答礼,日本派遣使者前往元朝。
后来,日本也无法否认曾有日本使者入朝元朝一事。元朝与日本的实质性接触,可能发生在第3、4次遣使之际。至元五年,黑的、殷弘等人与高丽的申思佺、潘阜等人在前往日本途中,到达对马时,遭到当地官员的袭击,使者们绑架了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并带回高丽。笔者推测,被绑架的二人可能是对马地方官府的下级职员。塔二郎、弥二郎在大蒙古国国都(中都)受到元世祖的召见并问话,二人向元世祖传达了感谢之情并得到优待,被准许返回日本。塔二郎、弥二郎被送还日本,而且高丽金有成向日本传达了大蒙古国的旨意,这就是第4次遣使活动。在元朝远征日本前的两国外交关系中,日本持续受到外国的压力,鲜有对外发声的机会,可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弥四郎为代表的数名日本使者,再到后来的塔二郎、弥二郎,他们最终均杳无音信。因为蒙古入侵日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被军事侵略所遮蔽,此次两国的外交交涉轶闻可能在日本史籍中被抹杀,否则不至于没有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