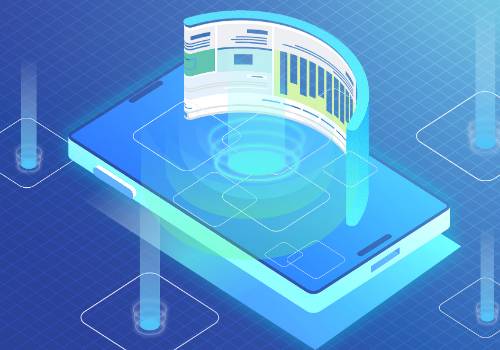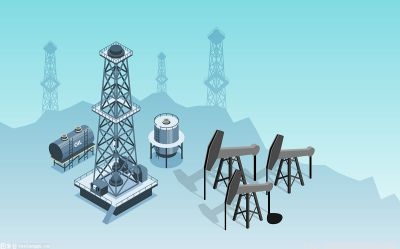回顾李叔同的一生,两次重要的人生转向格外醒目。本篇文章即从李叔同的诗词进入,由此透视其人生中的这两次重大转向。
 【资料图】
【资料图】
秋九月初四日,岁在壬午,西历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晚晴室圆寂,在圆寂三天前,他写下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四个字:“悲欣交集”。
没有落款,亦未署年月,笔迹散落孱力,可见当时病体已然势不能支,但依然可以看出是他的亲笔。这是他对一生的总结吗?抑或是他最终的了悟。如果此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那么在经历种种之后,最后的了悟,本就是对此生此世的总结。因为,这是用一生才能领悟到的禅机妙道,对佛门弟子来说,也是能带往别一个世界的唯一东西。
弘一法师出脱尘世,如今已有八十周年,作为书画家、音乐家、文人、高僧,他的印迹却并未随着肉身的灰灭而消散,反而如种在人心的灵根,生根发芽,尽管绽放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未必尽如法师当年所愿,对他焚香礼拜者,未必皆是诚笃信士,种种贪嗔欲念,也常常披服虔敬的伪装。迷信与诚挚常常只有一步之遥,一如执念与坚毅往往是一枚钱币的两面。
但相反之物,往往也互相成就,因有所失而悲,因有所得而欣,得失之间,亦是悲欣之因,悲欣之因,有的只会成为一时的情绪,随生随灭,有的却会成为成就自我的法门,迈过这一道门槛,便是了道彻悟之境。
悲欣交集,是人生,也是法门,种种因果轮转,一世轮转,终归如一。非不知众生皆苦,三界火宅,非不愿脱离此世此身,终归涅槃妙道,然而既来此一生,便从苦中了解种种有情之利乐,唯有明了众生愚痴执念,方能明了何谓解脱之道。
或者,本不求解脱,亦无所谓解脱。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是故,悲欣如一。
回顾李叔同的一生,两次重要的人生转向格外醒目。1918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完成了“政治-文艺”与“文艺-宗教”两次人生转向。这两次转向究竟为何会发生?当斯人已逝,他留下的诗词就成了今天的读者走进其内心世界的通路之一。本篇文章即从李叔同的诗词进入,由此透视其人生中的这两次重大转向。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30日专题《悲欣交集》的B04-05版。
撰文 | 郑欣怡
在清末民初仁人志士中,李叔同(1880-1942)表面与其他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求学之路,却在1918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完成了“政治-文艺”与“文艺-宗教”两次人生重要转向。李叔同为何会发生如此转变?为何他无法像其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度过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间的黑暗期?皈依佛门后他是否找到了面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破解之道?
“内融型”思想,
悲壮与悲婉的两种情感模式
从思想史层面展开讨论,或许能探寻出一条幽微却关键的脉络。
无论是艺术理想还是宗教精神,李叔同具有较为稳定、隐蔽的思想特质。笔者将其概括为“内融型”思想,即思绪少向外明显表露,情感指向以落于个人层面为主,呈现出脆弱、少坚韧性的特征。以李叔同忧国诗词为焦点,分析其情感模式与蕴含于中的“内融型”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李叔同遭遇政治理想、艺术追求破灭的两次精神危机。这些危机与思想特质之间相互缠绕,构成一幅复杂图景。如果将视野放宽于中国现代性进程,李叔同式的精神自我救赎之路则会带来别样的启示。
李叔同早年忧国诗词的两种情感模式——悲壮和悲婉——给予了我们把握其“内融型”思想的方式,即悲哀家国不再却缺少为何国破与如何救国的思索。
李叔同悲壮走向的忧国诗词多依外事推力而作,勾勒出晚清国破图景,却也止步于此。1901年由沪返津,正值《辛丑条约》签订,李叔同写下《感时》:
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遑敢望千秋。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在此,“杜宇”、“故国”、“愁”、“将军”和“断头”,描摹出了战争后的荒芜冷凄与内心愁绪,同时“男儿”意欲牺牲效国的激昂之情呼之欲出。但不难发现,这种“将军/断头”壮举,实际上恰恰影射了诗人内心对国破惨景的无力与焦虑: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真正拯救大清王朝,只能回归最古老也最直接的答案——献出生命,将救国报国落于笼统化的个体“男儿”,构建出“英雄神话”。
并且,这其中有日本上冈君对李叔同“尽忠报国”的告诫在内,后者听此“感愧殊甚”,才作出《感伤》一诗,因而其中有外力成分促成。而李叔同追随过的戊戌变法大将梁启超,庚子事变时表现为:“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著论、民权、哲理,展露出诗人崭新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并且包孕着行动力,呈现出与李叔同相反的写作心态和思想内质,构成了时代断裂期的双向轨道。
如果说悲壮倾向的忧国诗词表露出李叔同“内融型”思想的个体性,悲婉风格则指向了其脆弱的一面。无论是回津探乡时的《夜泊塘沽》(1901)“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还是《喝火令》(1905)“故国今谁主,胡天月已西。朝朝暮暮笑迷迷,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都悲哀、凄婉、迷离,但也仅仅是哀叹而已。
李叔同,1896年摄于天津。
倘若说,梁启超等政治倾向明显的知识分子与李叔同进行比较尚不足以论证后者“忧国诗词”只悲不叹的特征,那么与李叔同具有相似经历的鲁迅,便为李叔同“内融型”思想再添力证。鲁迅留日求学期间诗词作品数量有限,但为数不多中就有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壮,不仅点明故国风雨飘摇,也将救亡落在了实处的“我”的行为上而非缥渺的“英雄”。
因此,李叔同诗词中拳拳哀国心显见,拳拳报国行却不见踪影,不断的哀叹、泪流、悲戚弱化了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愤懑与壮志,显现出李煜式的亡国之悲,这也是李叔同“内融型”思想的外化体现。这种“内融型”思想也预示着李叔同似乎无法抵抗之后的两次精神危机,也无法完成五四运动前漫长黑暗期中俗世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救国”与“念佛”,
在乱世之中形成逻辑圆圈
将时间拉长,晚年的李叔同,在面对日军入侵的又一次国破家亡之危时,强烈忧国情喷涌而出,激昂诗风盛如当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李叔同对“英雄神话”的依赖明显可见减弱,“内融型”思想韧性提高,救国的自我显现。选择佛教作为自身个体精神救赎的方式后,李叔同同样在救国之路上找到了支撑。其中最为出名的即“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警语。
明显地,在李叔同这里,“救国”与“念佛”两者被联结,在乱世之中形成逻辑圆圈,其中“必须”一词呈现了佛门中人弘一法师对宗教救赎力量的强烈推崇,不仅能救人于精神危机中,而且能救国于民族危亡时,念佛的价值与合理性在此显现。1941年腊月,李叔同“赴泉州百原寺,又至开元寺小住;值结七念佛”,又一次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特加题记对此做出阐释:“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增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佛法的启蒙觉醒之力被凸显,“念佛—救人—救国”的逻辑链条完成,忧国忧民之情蕴纳其中,这种落于实处的个人之为而非缥缈的“英雄神话”,给予了浓烈爱国情感以皈依,虽思想特质仍为“内融型”,但显露出解除精神危机后的不迫与坚定。更为激昂的情感外化体现于《为红菊花说偈语》一诗:
诗序:辛巳初冬,秋月凝寒,贯师赠余红菊一枝,为说此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红菊花”亭亭,颜色“殷红”,向世人展现“高标”、“劲节”,由此引向乱世国破中的“我”,要做的便是“流血”“殉教”。短短五言绝句,悲壮、凛然、激昂等情感混而融之,似破土春草聚而涌现。这首抗日战争时期的明志之作,成为了李叔同诗歌写作生命的绝笔。
弘一法师,李鸿梁摄于1931年。
此时的李叔同,已不再如晚清时期面对国破家亡,无力悲叹只能寄托英雄造化,而是自我精神危机消逝后,个体力量彰显,如同梁启超的“三民”学说,殉教报国成为了家国危亡时李叔同具有个人思考特色及可行动性的救国之举。这种激进的、自我牺牲的个体式挽救国家民族的决心与意念,李叔同在1939年致信中曾有表明:“对付敌难,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浓烈的忧国情感在诗词中涌动,促使李叔同在宗教世界里完成个体救赎后,其“内融型”思想落于实处,生发出独特力量,仿若鲁迅“反抗绝望”精神内核所具有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不过明显地,忧国诗词的“悲婉”情感模式在李叔同晚年创作中被有意规避与隐藏,在其入佛后的其他晚期文学创作中,更多显现出的是兴然趣味与淡然含蓄之韵。对于绮丽之词的摒弃,是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于诗词创作上较为明显的转变,从《护生画集》配诗上即可窥见晚年李叔同的思想旨趣。《众生》中“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为爱物”的佛家仁爱,《生机》中“小草出墙腰,亦复饶佳致。我为勤灌溉,欣欣有生意”的恬淡悠然,《解放》中的“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至仁所感,猫鼠相爱”的智慧平和,多棱面地丰富了李叔同诗词创作风格,同时也勾勒出宗教救赎自我后逐渐坚定平和的“内融型”思想世界。
弘一法师的印章“一息尚存”,弘一法师俗名为李息。
因此可以说,一代传奇大师在风云变幻的六十年里,为时人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别样的道路启示与立身指引——宗教成为了破除乱世现代性突转困境的途径之一,并能够实现个体精神的自我救赎,乃至某种程度上借此以救赎他人。
李叔同早期忧国诗词中呈现出悲壮与悲婉两种情感模式,同样“只悲不思”,即忧国哀民却只能依赖英雄神话并流泪凄然,因而凸显出向内的、个体性的、脆弱无力的“内融型”思想底色。这一思想特质与李叔同“政治—文艺”与“文艺—宗教”的人生转向紧密相连,精神危机就此产生。拯救民众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希望落空,“内融型”思想又促使李叔同走向了宗教自我精神救赎,并为面对中国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别样的启示。
诗词笺注
/ /
《菩萨蛮·忆杨翠喜》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作于1905年,最初见于《南社丛刊》第8集,1914年3月版。署名李凡。
/ /
●燕支山:①隋志:武威郡番禾县有燕支山。②又叫胭脂山、焉支山,在今甘肃省山丹东南。以其多产燕支(红兰花)而得名。③《全唐诗》卷六二杜审言《赠苏绾书记》:“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
此处喻指歌伎聚居的地方,诗人想借“燕支山”表达对杨翠喜的回忆与思念。
●晓风:①晨风。②典故:柳永《雨霖铃》:“杨柳岸,晓风残月。”唐琬《钗头凤:“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晓风”成为诗词中表达愁思、相思、回忆等情绪的常见意象,诗人此处借此流露其悲哀,借景抒情。
●游丝:①蜘蛛等昆虫所吐的飘荡在空中的丝。②典故: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晏殊《诉衷情》:“此情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严仁《玉楼春·春思》:“意长翻恨游丝短,尽日相思罗带缓。”
“游丝”的“短”,衬托出“情”的“长”,但中间“忘却”一词,却表现出情意绵长但现实离别的无奈。
●杜宇:①又名杜鹃、子规,鸟名。鸣声凄历,能使旅客起思乡之念。②典故:朱淑真《蝶恋花·送春》:“绿满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苦。”释祖钦:“尀耐深山百舌,也学江南杜宇,声声报道不如归。”
杜鹃鸟也是诗词中表达思念、伤痛、愁绪的重要意象之一。“酒醒”时“月痕低”,加之前面提到的“晓风”,可推断此时是破晓之时,分别之痛、相思之苦便萦绕在声声杜鹃啼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