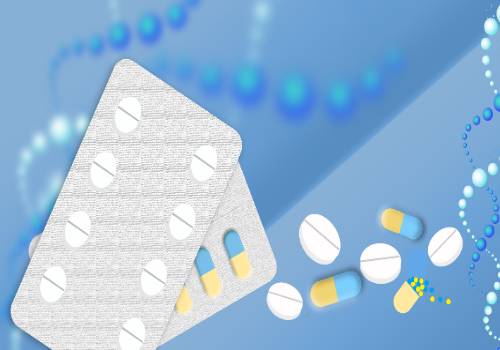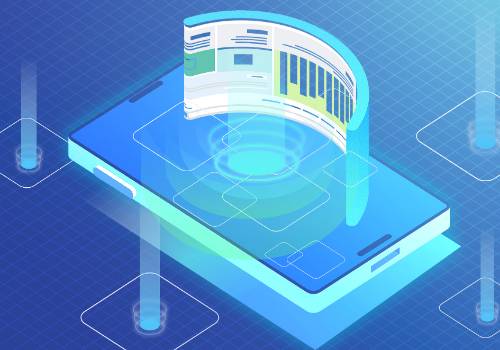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天主教和沙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机枪大炮的保护,大规模地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信徒,收集情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起到了机枪大炮起不到的作用。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晚清教堂
教堂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传教士与大清官员按对等职位平起平坐,当时清廷规定:“主教”与“总督”“巡抚”平行;“副主教”与“藩司、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
老百姓对县太爷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老爷的妻子叫“太太”,三品以上高官的老婆才可尊称为“夫人”。主教的老婆等同于中国的“一品夫人”,牧师的老婆等于“太太”。一般老百姓见了他们都要下跪。
教会霸占百姓田产,包揽词讼,干涉行政,甚至自居为一方之主(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非法组织武装,收买地方败类作爪牙,鱼肉乡民。当时入教的,既有受蛊惑的贫苦百姓,也有不少地主、恶霸和流氓分子。他们在教会的庇护下,作奸犯科,无恶不作,激起民众的普遍愤慨。
传教士
19世纪末,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达3200人,建立教区40多个,教会60多个,入会教徒80余万人,仅山东一省就建有教堂1300多座,遍及全省七十二个州县,有传教士三百多人,发展教徒八万余众。其中以天主教势力最大。天主教在济南、烟台、兖州设立总堂,以之为基地,指挥和联系分布在全省各地的教堂。作为侵略活动的据点之一,鲁西南地区的教堂是由兖州教堂指挥和联系的。
巨野所处的鲁西南是德国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当时巨野县内有天主教传教点21处,中心教堂设在城东七公里处的磨盘张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长驻此地。薛田资身材魁梧,头顶半秃,眼泛绿光,生着一把又浓又黑的大胡子。他以传教为名散布所谓的“教义”,麻痹民众思想,帮助国内搜集情报,为其侵略开道。还勾结官府,强占民田,侮辱妇女,无恶不作,在当地名声很坏。
薛田资
刘德润,巨野县独山镇小刘庄人。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好本领,一把大刀使得出神入化,人送外号“刘大刀”。他性格豪放,交游广泛,朋友遍及三教九流,和大刀会的一些头领往来密切。
鲁西地区过于稠密的人口,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迅速恶化的经济状况导致出现了大量赤贫者,他们经常聚集起来抢劫,将抢钱叫做“请财神爷”,绑票富人家小孩叫做“抱凤凰雏”。刘德润也参与过此类行动,有个名叫魏培喜的拜把子兄弟常给他打下手。此人一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钱不够用时,就去找刘德润借。刘德润为人豪爽,对兄弟义气,有多少给多少。但他终年以打拳卖艺、兜售膏药为生,手里也不富裕,不是每次都能满足他的要求。为了多弄钱,魏培喜就投靠了巨野知县许廷瑞,在其手下充当了一名捕快,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从此二人关系逐渐疏远。
魏培喜好吃懒做、拈轻怕重惯了,在衙门混了一段时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做捕快工资不高,他又没立下什么功劳,自然得不到奖赏,靠领点死工资哪里满足得了他的高消费?没过多久又变得囊空如洗了,只好厚着脸皮又去找刘德润借钱。
那天傍晚,刘德润拖着一身疲惫从外面回来,刚进院门,身后就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刘哥,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吗?”扭头一看,正是自己以前的拜把子兄弟、如今的衙门捕快魏培喜。
一见是他,刘德润就不大高兴,板着脸说:“还凑合,有什么事吗?”
“没有事,就不能来了吗?”魏培喜笑嘻嘻地说,“大半年没见,兄弟我都想死你了。”
刘德润一听这话,心头一阵厌恶,又不好撵他走,只得放他进来。
二人进得屋来,刘德润的老婆和女儿刚好把饭菜端上桌子。
刘德润问:“你吃饭了没?”
“还没呢。”魏培喜说。
“那就一起吃吧。”
魏培喜正巴不得,道了声谢就上了桌,边吃边夸道:“好久没来大哥家吃饭了,嫂子的手艺还是那么好。”
刘德润的老婆笑着说:“你过奖了。”
“没有,嫂子的手艺是出了名的。哟,多少日子不见,侄女都出落得这么漂亮了。”魏培喜故作惊讶地望着刘德润的女儿说。把小姑娘羞得满脸通红。
“闺女长得丑,兄弟见笑了。”刘德润的老婆说。
“不要谦虚嘛,侄女条件这么好,将来准能许配个好人家。”魏培喜说。
一边吃饭一边叽叽聒聒地说个没完。
饭后,刘德润的老婆和女儿把碗筷收进厨房去了。
两人坐在凳子上聊起了天。
“你最近在衙门怎么样?”刘德润面无表情地问。
“唉,别提了,衙门管得忒严,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应卯,累死累活也挣不到什么钱,还不如以前逍遥自在。”魏培喜连声抱怨道。
刘德润没有搭腔,心想这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我最近赌博又输了,欠了不少钱,到处都有人在追债,日子不好过啊。”魏培喜可怜兮兮地说,两眼巴巴地望着他。
刘德润知道他多半又要问自己借钱,皱着眉头说:“不好意思啊,兄弟,我闺女马上就要嫁人了,这段时间在给她准备嫁妆,现在我手上也很紧,可能帮不到你。”
魏培喜一听就急了,说:“你我兄弟一场,这点小忙你都不肯帮吗?”
刘德润说:“不是不帮,真是有心无力,要不你上别处去问问吧。”
“只借一吊,就一吊,翻了本,马上还给你。”魏培喜用乞求的口吻说。
刘德润心里冷笑:你小子在我这儿借过多少次钱,什么时候还过?我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德行?摇着头说:“我现在手上半吊钱也没有。”
魏培喜一脸怀疑:“不会吧,你今天刚收了摊回来,怎么着也有个一两吊吧。”
刘德润见他不信,把腰间的荷包取下来,解开拴口的绳子,将铜钱全部倒在桌上,对他说道:“你看看吧,这就是我今天挣的钱。”
魏培喜定睛一瞧,果然只有两三百个铜钱,大出意外,难以置信地说:“现在生意就这么难做了吗?”
刘德润说:“可不是?而今年头不好,大家手里都没钱,能混碗稀饭吃就算不错了。再这样下去,我都要准备改行了。”神色有点忧愁。
琢磨了一会儿,魏培喜兴奋地提议道:“大哥,要不咱组织人马再干以前的老本行,那个来钱倒快。”
刘德润横了他一眼,说:“亏你想得出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哪里还能干,那是要遭报应的。你现在又是专门抓这个的,这不知法犯法吗?”
魏培喜不以为意道:“没事儿,跟兄弟伙打好招呼就行,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这年头,能挣钱才是硬道理,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刘德润听了,心里一阵鄙夷,说:“要干你找别人去干吧,我是不干了。”
“你真打算金盆洗手了?”
“我想过点安定日子,不想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地过了,还望兄弟见谅。”
魏培喜见他既不肯借钱,又不愿跟自己去绑票,心头大为恼火,扯了几句,就气呼呼地走了。刘德润也懒得送他。